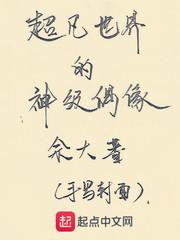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阴戏 > 第33章(第1页)
第33章(第1页)
我看到那个大红旗的车门打开了,从车上一连下来好几个人,有年纪大的,也有年轻人,都穿着当时干部穿的那种四个口袋的军绿色外套,他们的身上都没有佩戴军徽,所以我看不出他们的军衔,但从他们那种后背笔挺的身姿来看,这几个人肯定都是军人,从车门一打开他们就跳下车的那种利索劲儿来看,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,说不定只是车里坐的那个人的警卫员。我开始猜想车里的那个大人物是不是哪个军区的首长。
我的心里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对劲。
我之前说过,我们这里的山路不好修,村里尽管有了钱也不愿意修路,是因为这条进村的土路很陡,即使修好了,一般汽车也没法开进来,必须得重新开山开路,这个费用就不是村里承担得起的。而且我们这里要到外界,先要过渡口,走一段水路,哪怕把路修得再好,汽车过不了渡口(我们这里的渡口都是乱石滩,秋冬季节水浅,船不吃水,有时得靠人拉,因此吃不得重),也是白搭。所以哪怕是现在,我们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汽摩,村里鲜少有人开车的。要搁在十年前,我小的时候,那汽车就更是稀罕物件了。村里的老人,如果不进城去,恐怕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汽车。
因此要搁十年前,我那么小的时候,村口停了一辆轿车,而且还是一辆大红旗,那绝对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,但居然没有一个人提起过,这就很不对劲了。
这辆大红旗,要一路开进我们村来,肯定要费不少波折,一路上肯定会有不少人看到这辆大红旗,别的不说,就说过渡口:以这辆大红旗的吨位,这么个六米乘三米长宽的大家伙,过乱石滩子的时候,必须得好几个船家一起拉纤才行,那种热闹的大场面,当时肯定得有许多人围观才对,可在我的记忆里,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辆大红旗?
如果说我当时只是一个孩子,不理解这辆大红旗有什么稀罕的地方,可我们这儿的那些大人们呢?那些村干部们,那些镇上文化站的人们,他们会从来没有听说过大红旗?他们会不知道来的是哪一位大人物?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,突然来了一位首长级的大人物,坐着一辆神气的大红旗,这样的事,哪怕搁在今天,都是足以成为传奇一样的事,能叫兆旺这样的人,站在村口吹水的时候,吹上一遍又一遍。谁能够忘记这样的事呢?如果说我当年只是一个浅薄的孩子,偶然遗忘了这辆大红旗,尚且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,那么整个村子的人们都不记得这辆大红旗,这事情就很古怪了。
是什么样的力量,能够让全村的人们都集体失忆?
我望向我背后的村子,那应该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村子。村口的铺子都门板紧闭,空荡荡的档口上面贴着褪色的红纸头,整个村子被笼罩在一层淡蓝色的晨曦中,显得十分静谧,就好像全村的人都睡着了,没有一个人醒来,没有一个人出来溜达,除了我和我的小叔叔,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一天的清晨,村口居然停了一辆大红旗。
我突然想到尼克松访华的那一年,当时为了避免他的访华团跟我国人民接触,整个北京城的人都要延长上班和上学的时间,平时五点下班、放学的人,都要被关在单位、学校里,要被关到晚上八点,才放他们出来,让他们上街、回家。这样尼克松走在北京城里的时候,他看到的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北京城,大街上几乎一个行人都没有,他不禁觉得很奇怪:这座城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?
我心中的疑问也跟尼克松一样:人都到哪里去了?
我知道某些到了一定级别的政要,他们出来肯定要戒严,这就跟古代官老爷上街,前面要有人开道,竖两块“肃静”“回避”的牌子是一个道理。可我也知道,以我们这儿人的秉性,哪怕是戒严,不让他们上街,让他们哪怕醒了,也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乖乖待着,他们也肯定会躲在门板后面偷看,更不用说那些个赖子,还有稍大一点的、有点懂事的小孩子,那他们肯定更要想方设法地找个可以偷看的地方了。
可我却能感觉到,这些铺子的门板后面是没有人的。
人气,这个说法很玄,但我确实没有从那些铺子的门板后面感觉到有什么人气。其实人气也可以说是人身上的气味。如果那些门板后面有人在偷看,那么多的人,他们身上的气味混合在一起,那一定是一股非常大的味道,我的鼻子虽然不如狗那么灵敏,但也一定会有所感觉。可是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。
我突然想到,或许整个村子的人,都不记得这辆大红旗,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,那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这辆大红旗。
所有的人都被撤走了。在这一天的清晨,在大红旗出现在村口的时候,整个村子里只有我和小叔叔两个人。
我的小叔叔已经发散了,他像个真正的戏疯子那样把自己吊死在了古戏楼上。现在只剩下了我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是唯一记得这辆大红旗的人了。
我站得远远的(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站得远,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事物离我也远,我看到那辆大红旗停在村口,离我大概二十来步的距离,我没办法再靠近了),我看到那辆大红旗的车门打开了,又下来一个人,看上去大概四十来岁,也是穿着那种四个口袋的军外套,这个人看上去的军衔应该要比其他人都高,因为刚才下车那几个人,见到他虽然没有敬礼,但是后背都下意识地一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