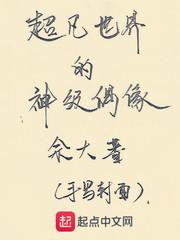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阴戏 > 第87章(第1页)
第87章(第1页)
我这几天跟戏班子混得熟了,知道他们是从梅山那边过来的,戏班子里的人基本上都姓邓,老头叫邓五丰,算是班主,那个拿衣服给我穿的年轻人叫邓福星,是老头的儿子。扮观音的是戏班子里唯一的女人,叫邓六月,是老头的亲妹妹,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,我头回看到她卸了妆的老脸简直吓一跳,跟台上那个俊俏的观音完全就是两个人。那个扮童子的其实是个侏儒,是她的伙计(没结婚但在一起搭伴过日子的男女)。还有一个叫邓八尺的琴师,是老头的弟弟,今年过五十岁,是戏班子里除了邓福星之外,年纪最小的一个了。
戏班子生火烧水。邓六月做饭,给演观音得道时割脖子放血的死鸡褪毛。邓老头走过去,把锅子揭开看了一眼,又从袋子里多抓一把米进去,说:“多一张嘴吃饭,不兴叫人饿着。”
我听了心里一暖。
几个男人围着火抽烟。邓福星比我小两岁,长得很是白净,说话也斯文,听说我是大学生,还是在北京上的大学,就一直找我聊天,问我有没有去过天安门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,离家最远就是去安化念中学那会儿,后来没考上大学,就回家了。邓老头晚年得子,把他疼爱得很,不叫他跟着戏班子学戏,也不许他出去打工,叫他只管读书,重新再考。这次跟戏班子出来,还是他求着老头的。
邓福星说:“要不是拐子心思不在学戏上,我爹这次还不肯带我出来啰。”
我才知道原来在盐皂村跑掉的那个邓拐子是邓福星的堂哥。老头想把本事传给邓拐子,但是邓拐子嫌苦,赚不到钱,一直不情不愿的,那回让他跳吊吊,他原本就不乐意,跟老头争了几句,一生气就索性跑了,留了个字条,据说去打工了。
我心想这也正常,现在的年轻人,还有哪个想学唱戏的,尤其还是目连戏。
邓老头说:“我今年六十八岁,邓家的苦目连要断在我手里了。”
邓福星说:“爹,我跟你学么。”
邓老头说:“你好好念你的书。”
邓福星说:“我不是那块料,都考了三年了还没考上。”
邓老头说:“你也不是学这个的料。你不比拐子,你学我的本事是要吃苦的。”
邓福星说:“爹,我不怕苦。”
邓老头说:“你还不如他适合,他能看见的东西你看不见。”
邓福星看到老头指着我,吃了一惊,看着我,眼神居然有些嫉恨。
我低下头去,摆弄手腕上的大罗马表,避开邓福星的视线,走到了一旁去。
邓福星压低声音说:“爹,你的本事又不传外人。”
邓老头说:“那倒是。”
邓福星说:“那你就教我呗。”
邓老头说:“你真想入这个行当?苦目连不比别的戏,别人有事请你去唱戏的时候殷勤,没事的时候见到你就绕道走,把你当瘟神一样躲着,你愿意?”
邓福星说:“那是他们怕你的本事。我就要学这个本事。再说了……”
邓福星看了我一眼,把声音压得更低了。我听不见他说什么,只听见邓老头最后叹了口气,说:“那个事没个准的,倒是你,学了就不能后悔了。”
邓福星看老头答应了,脸上高兴得很,也不再找我说话了,吃完饭之后,就早早地睡了。
我也学着戏班子的人,进了棚子之后拿块塑料布把自己给紧紧地裹住,和衣躺在泥地上。棚子没有顶,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,冷风一吹,塑料布就哗啦哗啦地响,吵得很。戏班子的人倒是习惯,很快就都睡着了,就连邓福星都打起了鼾。
我睡不着,就胡思乱想。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过得苦,没想到世上还有人比我更苦。可我就想不明白了,这个戏班子的日子过得那么苦,为什么邓福星还想是一心学戏?我跟着这个戏班子,想偷偷学本事,是想要对付五老爷和白师爷,邓福星求着他爹学本事,又是图啥?难道他是想学会了放猖好去害人讹钱?可我跟他说了几天的话,觉得他也不像是有这种坏心眼的人。
算了算了,我连自己的事都没琢磨清楚,还去琢磨别人的事干什么。
我迷迷糊糊睡着了,睡到下半夜,被小话皮子刨我头皮给刨醒过来。
这小畜生的翅膀已经养好了,不肯再吃我喂它的米,我就放它自己去找吃的。起先我还拿绳子拴着它,后来看它已经把我脑袋当成了窝,自己会回来,我也就不拴它了。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飞回来的。
我怕小话皮子兴起,半夜里来一段《贵妃醉酒》,把戏班子的人都给吵醒了,就连忙支起身子,一把捂住脑袋,把小话皮子给捏在手心里,却见棚子里静悄悄的,连打鼾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
一阵风吹过,几块扔在地上的塑料布卷成一团,哗哗作响。
我猛地坐起身来,棚子里除了我之外,一个人也没有。
整个戏班子的人都不见了。
孩儿岗
我赶紧冲出棚子一看,戏班子的勃勃车还停在老地方,熄了火的炉子也还没收拾,就搁在棚子外的地上,一切就跟我进棚子前睡觉一样,什么也没动。
我松了口气,我刚才心里面的第一个念头,就是戏班子撇下我一个人走了。
其实戏班子跟我非亲非故,不管他们是撇下我走了,还是发生了什么事,全部人都失踪了,也都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我混在这个戏班子里头,无非就是想躲过五老爷的眼线,顺便偷学本事。可不知为什么,发现戏班子的东西都还在,知道他们没把我给撇下,我心里居然感到了一阵安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