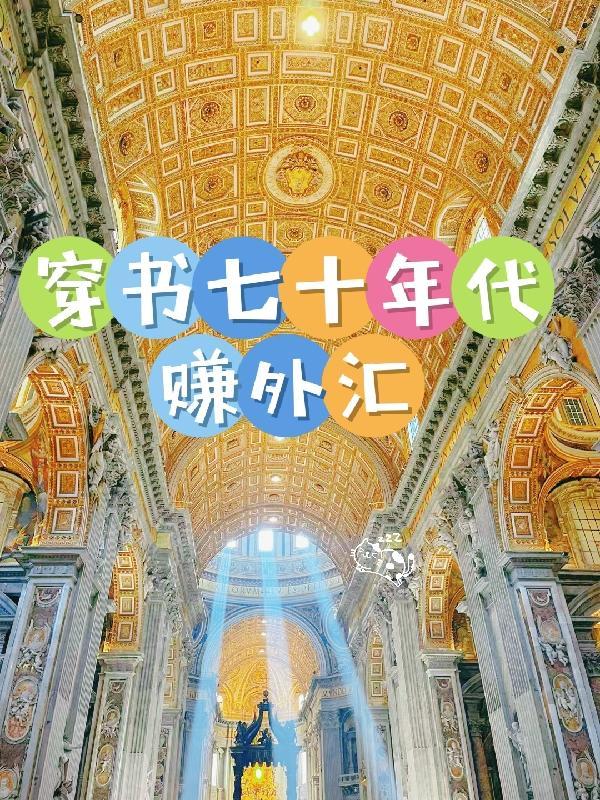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怂包女配的恶毒婆母重生后 > 第5章 夫人真是太爱他了(第1页)
第5章 夫人真是太爱他了(第1页)
她还记得上辈子这个时候生的事。
那时候,她远在南疆的养兄还不曾出事,日子风平浪静,她同意白玉凝留在府中之后,白玉凝便每日同柳烟黛来一起给她请安。
柳烟黛的性子——便不再提了,单说说白玉凝。
白玉凝是个极讨喜的姑娘,灵动聪明,又生的清雅,腹有诗书,最关键的是,她生的又像是她的母亲,秦禅月的好友,秦禅月因此颇为喜欢她。
这也是为什么,白玉凝能在府中勾来两个少爷的原因。
秦禅月想起上辈子的事后,心底里暗暗多了几分怀疑。
上辈子既然没病,这辈子怎么又有病了?
偏偏这个时候病,瞧着可不像是病,而像是留在侯府中的手段,毕竟她都病的要死了,秦禅月却依旧命人将她丢出去,这不合礼法——别看秦禅月背后动手凶猛,但面子上向来做的好看,真要是演起来,也不曾叫人拿了把柄。
上辈子秦禅月不曾说什么重话,可能给了白玉凝嫁给周渊渟的希望,但是这辈子,秦禅月已经将话说死了,白玉凝应当知道不可能嫁给周渊渟了,为何还要费尽心机的留在侯府?
“去寻个大夫好生查查看。”她拧眉吩咐了一句后,又道:“再寻两个人,暗处盯着她。”
下面的丫鬟应声而下,秦禅月则起身去了一趟小厨房,亲手做了一碗金丝火煲老鸡汤,装进檀木食盒里,端着送去了周子恒的厢房间。
她嫌周子恒死的不够快,打算再去加点料。
秦禅月本来是与周子恒同房而住的,她自认为他们俩相知相爱,当生同衾死同穴,所以除了葵水期从不曾与周子恒分房,直到这一日,重生回后,她便以“葵水来了”以理由,与周子恒分住了。
现下周子恒住在东侧一处厢房间,行过回廊便可推门而入。
厢房前做了窗景,为假山翠竹,青苔攀爬,一推开木窗,便能瞧见窗外翠竹摇晃,飒踏青石板。
秦禅月穿过假山,裙摆沾着翠竹的草木清香,手中提着食盒进门来时,正瞧见周子恒在丫鬟的服侍下起身,动作僵硬迟缓,似是还有些晕,一双温润的瑞凤眼与人对视的时候都有些恍惚。
“夫君——”瞧见他起榻,秦禅月一脸慌忙的放下手中的食盒过来搀扶,一张明艳艳的尖俏面上满是关怀,语调轻柔的问他:“夫君病重,怎的还下榻了?”
周子恒借着她的手臂站稳,捏了捏眉心道:“我尚有公务。”
他其实并非是有公务,而是到了下午时候,该去陪方青青了。
他的青青柔弱不能自理,他一日不去见都不行。
“可夫君还病着,大夫说了,夫君这个病就是太过劳累,再加昨日有雨,染了些风寒,若是不加小心,日后是会病重的。”秦禅月面上越心疼,扶着他道:“公务便歇一日吧。”
瞧着秦禅月的温柔软意,周子恒本欲离去的心也被留下了。
罢了,看在秦禅月这般殷勤伺候,他今日便不去陪方青青了。
周子恒已经站起来的身子便随着秦禅月的手重新倒下去了,秦禅月伺候他重新回榻上躺下还不够,还亲手将一旁的食盒取来,用羹勺来喂周子恒。
今日的秦禅月穿了一身浓翠色对交领锦缎长裙,腰间缚以镶金嵌玉的红丝绦,她生的丰腴,若饱满的桃花,这样充满肉感的身骨正好撑起那艳丽的颜色,红绿交错间,映出一张明艳的面来。
午后的烈阳被丝绢窗纱阻了一部分,只有一条细光线落进来,正好落到她的面上,将她艳艳的红唇与雪色的肌肤照出泠泠的光亮,满头金翠随着她的动作晃着熠熠的光,一眼瞧过去,便知道是个地位极高的贵夫人。
偏她在他面前从不摆架子,一见了他,她便软下枝丫,缠着他撒娇。
周子恒满意的饮了一口汤。
汤炖了很久,入口咸香,他躺靠在金枝玉软枕上,静静地品味。
饮过这口汤后,渐渐觉得头昏脑涨,格外困倦,顺势便闭眼休憩。
秦禅月静静地看着他熟睡的面,亲自替他盖好被子,轻轻拍着他的被。
周子恒渐渐跌落梦乡时,感受着身旁秦禅月放在他身上的手的重量与温度,不由得也感叹,秦禅月当真是太爱他了。
若不是爱他,如秦禅月这样高傲矜贵的人,又怎会如此伏低做小呢?
这一系列熨帖的动作落到旁的丫鬟眼中,也成了恩爱的证明。
“夫人对老爷真好。”
“老爷和夫人恩爱百年,实在惹人艳羡。”
秦禅月在一旁侯着他,待到他熟睡了,才从此处离开,只不过离开之前,秦禅月怕这里的丫鬟伺候不好她心爱的夫君,干脆将这里的丫鬟都换了,换成了她手头上的心腹,甚至连药都要她看过了才能端送到侯爷的床前去。
这样用心,谁瞧了都要赞一声好,家有贤妻万事顺遂。
这一趟走来,耗费了大概一个多时辰,秦禅月未时末才重回赏月园中。
忠义侯府极大,府内六进六出,东南角建有祠堂佛塔,中庭有高石照壁,自亭间绕开,远远可见一片莲花池,盛夏七月底,莲花正姣姣。
她前脚刚回赏月园,才刚坐下歇息,后脚门外便来了个嬷嬷,在外通禀。
“启禀夫人——”这嬷嬷是派去看着白玉凝的。
“嗯。”秦禅月抬了抬下颌,道:“说。”
那嬷嬷垂下头来,低声汇报道:“老奴回去后一直在暗处盯着白姑娘,白姑娘并未察觉到老奴,老奴瞧见白姑娘吞吃某种药物,似是借此伪造成[病重]的目的,而且,白姑娘今日还给上门来为她瞧病的大夫递了个纸条,老奴隔得远,不知道他们传递了什么。”
坐在案后的夫人渐渐沉了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