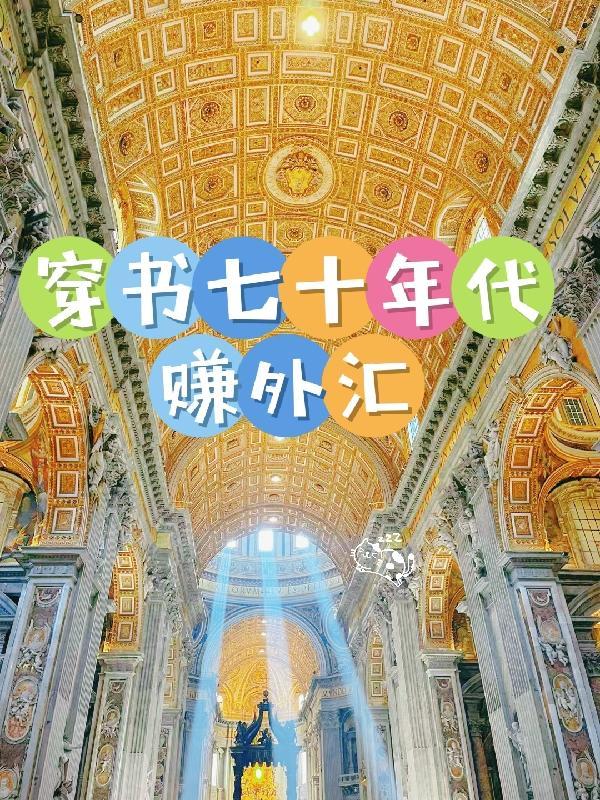笔趣书吧>枪气素霓生 > 第38章 虎威将军府上(第1页)
第38章 虎威将军府上(第1页)
既然霍鹏话他们可借道代郡,剩下那段路就顺畅多了,沿着并州边境缓缓前行,两个时辰后抵达代郡外围隘口,云堡!
云堡扼守山口,地势险要,驻扎着两千并州兵马。
堡上官兵见了张崇义所部,一言不打开寨门,由他们直行通过,既不阻拦也不问话,所有人都看向别处,就当没看见这伙人。
幽并两州毗邻而居,虽说分属不同的阵营,但向来井水不犯河水,很少生摩擦。
冬季应对青奴的袭扰,双方边军常常不经通报就能遥相呼应出兵,彼此惺惺相惜。
幽州富庶,自给自足有余,并州贫穷,军械粮草大头要靠朝廷拨付,边军常常缺兵少粮。
在镇北大将军府的授意下,有时候幽州兵马歼灭青奴小股骑兵后,会将青奴的军械粮草留给并州兵马,等于双手奉上后勤辎重军功。
此次幽州大规模出击青奴,无形中也替并州解决了心头大患,这个冬天或许可以安享几天太平日子,并州边军对幽州敬佩感激皆有之。
最初获知幽州兵马多路出击青奴,并州将军霍鹏和一众高级将领,想要趁机兵响应,选择的目标也是奇袭泉儿湾草场。
不过他们是临时起意,先要议定作战计划,再整合兵马,准备粮草军械,侦察泉儿湾草场的军情,浪费了几天时间。
好不容易万事俱备,已经接到幽州兵马摧毁泉儿湾草场的线报,霍鹏惊喜之余,立刻想到幽州兵马退路可能受阻,遂安排兵马悄悄在这土丘附近伪装等候,看看有没有机会帮幽州骑兵打次掩护。
吃人嘴短,拿人手短,霍鹏不是知恩不报之人。
有了这些历史渊源,镇北大将军张道冲在计算朝廷兵马时,才敢大胆的将并州兵马摒除在外。
他早就断言,并州即便出兵,也只会出动一些老弱病残,去到幽州无非是看戏。
顺利进了代郡地界,张崇义一行人才算是脱离险境,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可以放下,一路上再次有说有笑。
向烈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,开始拿菲诺逗乐子:“将军,现在没有性命之忧,这小娘们可以好好享用了,也不要选什么好时辰好地方,就在树林里把她吃了呗。”
菲诺始终要与张崇义同乘一马,此刻靠在张崇义怀里,一脸娇羞的瞪着向烈,小脸蛋绯红如霞。
张崇义无可奈何摇了摇头,不理向烈的玩笑。
过勒马河逃命的时候,干粮丢的干净,身上只剩水袋,一行一天没有食物,渐渐腹中饥饿,于是中途不再歇息,牵马昼夜不停赶路,在第二天黎明前到达蜂腰山口。
驻守士兵赶紧开门,迎接这支千里奔袭成功的凯旋之师,一个个热情洋溢。
蜂腰山口守将张清河前来跟张崇义叙话,这人是张家嫡系宗亲,张崇义的堂哥,两人同一个爷爷。
张清河情绪激动的拉着张崇义道:“你小子可以呀,千里奔袭,五天就到达战场,竟然一举偷袭成功。
我家老头子常常夸你是天生将才,从娘胎里带来的打仗天赋,我一直认为他言过其实,这次不信也得信。快跟哥哥说说,这一仗是怎么打的。”
张清河吩咐士兵给他们送上热饭热菜,众人饿了一天一夜,饥肠辘辘,二话不说就一顿狼吞虎咽,人人心里都有股劫后余生的侥幸。
张崇义简单跟他叙述此战的前前后后,张清河大呼过瘾,感慨自己没这么好命,被大将军安排坚守蜂腰山口。
张崇义抽空向他打探各路大军的军情战况。
张清河神色凝重,拉着张崇义走出营房,远离人群,悄声道:“这次战果不是很理想。
除了你们这一路大获全胜,奔袭蘑菇平原的上谷骑兵,虽然摧毁了草场,但返程时遭到青奴三万大军的围攻,六千精骑全军覆没,上下官兵悉数战死,拼掉了青奴近两万人马,可谓惨烈。
偷袭铁山屯的渔阳骑兵倒是烧掉了部分牧草,但青奴援兵及时赶到,牛羊马匹来不及烧毁,伤害有限,渔阳方面折损人马一千五百,狼狈逃回来了。
右北平那群蠢猪,竟然在草原里迷了路,迷迷糊糊逛了一大圈,无功而返。”
张崇义皱眉道:“也就是说青奴四大草场,两个全毁,一个毁掉一半,一个完好无损,损失人马三万以上,我们损兵折将一万二千?”
张清河点头道:“这笔账可以这么算。
从战果来看,我们自然是小占优势,加上勒马河谷那边,崇忠这小子可真是硬骨头,三万人马被十二万大军死死咬住,硬是拒险坚守谷底十八天,拼掉了青奴近三万人马,自己还能带着一万三千人逃回来。
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。”
张崇义一直挂念着大哥的安危,此时才如释重负,缓缓道:“战果自然是好看,但是没实现既定目标,算不上大获全胜。”
张清河哑然失笑道:“你小子这口吻跟大将军一模一样,大将军这几天一直黑着脸,黑鹰山口那边愁云密布。
听说昨天一怒之下,把右北平的骑兵将军给撸了。
我就纳闷了,此战以不到三万人马的代价,摧毁青奴两个半草场,消灭青奴各路人马近七万,可以说是三十年未有之大胜,你们父子怎么异口同声说不算成功?”
张崇义苦笑道:“清河哥,你说青奴还有没有南下袭掠幽州的实力?”
张清河愕然道:“青奴虽然吃了一些亏,远没有伤筋动骨,青奴大汗的主力骑兵仍在,还有两大草场作为后勤基地,动十万大军游刃有余。从兵力上来说,依然有入侵幽州的可能。”
张崇义直视着他道:“如果年后我们跟朝廷大打出手,青奴趁势兵南北夹击,你说会怎么样?”
张清河怔了一怔,干笑一声,为难道:“这倒是个麻烦事,我差点把这茬给忘了。
朝廷那二十万大军压境,单独应付倒不算困难,要是青奴趁火打劫,逼的我们两线作战,着实疲于应付。”
张崇义用更深邃的神色凝视着张清河,小声道:“再进一步说,假如我们跟朝廷大军死磕,青奴愿意坐山观虎斗。
等到我们击败朝廷大军,有青奴在后面虎视眈眈,我们又如何能够安心挥师南下,问鼎中原呢??”
张清河眼里释放出不可遏制的狂喜,颤声道:“大将军真打算逐鹿中原,跟大旗一较高下了?
我明白了,难怪大将军要不计代价去打青奴的草场,这是要毕其功于一役,打的青奴数年内不敢来东边骚扰。
要是这样说,这一战确实不算成功。他妈的,右北平那群蠢猪贻误大事,早知道是这样,我就应该跟大将军请令出击。”说着不停搓手,显然是心神激荡。
张崇义素来清楚,这些张家宗亲是最狂热最虔诚的南下派。
龟缩在幽州一隅之地,宗亲最为憋屈,毕竟巴掌大的地方,宗亲们能当个郡守就到顶了。